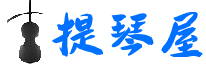巴伦博伊姆于1942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-俄罗斯移民,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超凡的音乐天赋。1950年,他的家人搬到了以色列,10岁时,他在维也纳和罗马进行了国际钢琴首演。随后收到了来自巴黎、纽约、萨尔茨堡音乐厅的邀请。但正是在1960年代的伦敦,他经历了“第一次真正的成人音乐体验”,他的指挥生涯才真正开始腾飞。

巴伦博伊姆对英国的喜爱也不可避免地与他的第一任妻子、大提琴家杰奎琳·杜普雷的记忆有关。他将于本月返回伦敦,为多发性硬化症协会举办两场音乐会,以纪念她死于该病30周年。“我在这方面的主要兴趣是筹集到足够的资金,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研究,”他解释道。“我们在研究中需要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:一个是找到更快诊断的方法,另一个是找到治愈方法。”
我让他画一幅他们在1960年代后期一起生活的图画,他从头开始。“这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故事,而不是通常的、浪漫的’他们在舞会上相遇,并看着[彼此]的眼睛’,一点也不,”他说。“我第一次和她说话[1966年],我打电话给她,因为我得了严重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和腺热症。”他计划在第二年与杜普雷一起演出,朋友们听腻了他的抱怨,告诉他他应该和她谈谈:她的病痛得更严重了。
“所以我给她打电话,她说,’哦,我很高兴和你说话,是关于音乐会的事情吗?’我说,‘实际上,不,我有腺热,有人告诉我你的情况比我严重得多。..’就是这样。”
几个月后,他们在伦敦的共同朋友(耶胡迪·梅纽因的女婿)钢琴家傅聪家中相识。“有室内乐演奏,在我们说话之前,我们坐下来一起演奏——我们演奏了勃拉姆斯奏鸣曲——并在音乐上完美地相互理解,然后在音乐之外也能理解。”她是“一位独特的音乐家”,他继续说道。“她对音乐学或科学方面的音乐知识并不十分了解,但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脑敏捷。她会第一次看到一首乐曲,她不仅能弹奏音符,还能触及它的精髓。”
这对夫妇于1967年结婚,被视为古典音乐界的宠儿。他们的故事充满了青春、魅力和激情——他们的浪漫可以与罗伯特和克拉拉舒曼相提并论。但不到两年,杜普雷就病倒了。“她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手术,完全没有任何困难,但她全身麻醉,当她醒来时,她身体的某些部位没有任何感觉,”巴伦博伊姆解释说。
很快她就无法判断弓的重量,到1973年她被诊断出患有MS时,她已经完全放弃了公开表演。他说,如果今天诊断出杜普雷,她的前景会更好(治愈方法仍然遥不可及,但绝大多数患者现在有12种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可供选择)但她的病情继续恶化,直到1987年去世,享年42岁。

与其他英年早逝的公众人物一样,杜普雷的角色现在充满了一种致命的脆弱感,回想起来很难估计这其中有多少。看着她表演的镜头,我被她的身体素质——她拉大提琴时的绝对力量和活力——以及她的轻松和幽默所震惊。
几年后,现在已经因MS的进展而虚弱的杜普雷(du Pré)以几乎令人心碎的辛酸反思了这一场合:“我们是五个朋友,因为我们的青春和共同创作音乐的乐趣而团结在一起。当我们演奏“鳟鱼”时,它会像所有音乐会一样消失,但克里斯托弗·努彭(Christopher Nupen)看了一部电影,突然间有一句关于我们永远幸福的宣言,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,它让我回想起那部分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永远是那么珍贵。”
杰奎琳·杜普雷Tribute音乐会将巴伦博伊姆带回南岸,他将与他的West-Eastern Divan Orchestra和年轻的奥地利-波斯大提琴家Kian Soltani一起演奏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。我对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没有出现在节目中表示惊讶——1962年,17岁的杜普雷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演奏了这首作品,使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,其悲惨的美丽几乎成为她生活的代名词和工作——但巴伦博伊姆说他会发现表演“在情感上是一种负担”。
“我记得[伟大的西班牙大提琴家]巴勃罗·卡萨尔斯(Pablo Casals),当杜普雷要在波多黎各音乐节演奏这首曲子时,他已经很老了,他告诉我,‘哦,我很期待这个,你必须知道——直到现在,没有人像杰奎琳那样演奏过这部协奏曲,以后也没有人会像她一样演奏,’”他说。据报道,卡萨尔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在杜普雷生命的尽头,巴伦博伊姆移居法国成为巴黎管弦乐团的指挥,并于1980年代初在这里与埃琳娜·巴什基洛娃建立了关系——然后是家庭——后者将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.无论是出于对巴伦博伊姆的尊重,还是出于对杜普雷的同情,媒体都没有报道过他在她晚年的缺席,而且他过去曾对他们的克制表示感谢。
巴伦博伊姆现在是音乐界的一个杰出人物。他成为拜罗伊特的常客指挥,并在1990年代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。但他作为钢琴家的成功,尤其是作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诠释者(自从他1960年在特拉维夫第一次完整的贝多芬奏鸣曲循环以来,他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奏)从未动摇过。
当我问到年轻音乐家的压力——经纪人的要求,自我推销的需要——是否比过去更具挑战性时,他以温和的贬低回应。“对于一个年轻的音乐家来说,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事情——比你问的更重要,是否因为媒体而更具挑战性——是生活在极度谦虚和极度自信的精神分裂症中,这一点没有改变。”他将这种谦虚定义为必须对作曲家的作品表现出的尊重,但补充说:“你需要有抱负,你不会坐在家里演奏,世界敲响了门铃,但理想情况下,抱负必须在至少比人才少10%。当野心大于天赋时,你扼杀了天赋,你扼杀了它。”
比方说,你是否像年轻时那样谦虚地对待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?“毫无疑问——在很多方面更多,因为我想我对它了解得更多一些。”

他举了最近在巴黎与国家管弦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例子。“我第一次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时,我演奏了这首协奏曲。那是在67年前的1950年,你不会相信我,我向你保证,有一些小东西——我不能说我对这件作品有一个革命性的新想法。”
自西东合唱团成立以来,巴伦博伊姆将大量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中东。该项目的发展源于这样一种信念,即疏远民族之间的音乐对话可以为社会对话铺平道路。“这个管弦乐队的基本原则非常简单,”他在2008年出版的《万物互联》一书中写道。“一旦年轻的音乐家就如何一起演奏一个音符达成一致,他们将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对方。”
乐团没有政治议程,但巴伦博伊姆本人有时也直言不讳。在6月访问拉马拉时,他在一场纪念六日战争50周年的音乐会上说,由于占领了巴勒斯坦国专用的土地,以色列正在失去“所有的体面和人性”。向我重申他的观点:“我发现以色列的占领是无法解决冲突的核心。以巴冲突不是政治冲突,也不是军事冲突,而是人类冲突,”他补充道。然而,他对这个地区的管弦乐队和年轻音乐家的信心丝毫未减。
在我的生活中,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,我不会通过它是否被普遍接受来判断我的所作所为
上个月,Pierre Boulez Saal——一个新的室内音乐厅,附属于最近在柏林开设的Barenboim-Said学院——以28岁的法国-黎巴嫩作曲家本杰明·阿塔希尔(Benjamin Attahir)的作品首演拉开了它的第一个完整乐季.“现在是我们的第一个赛季,大部分已经售罄,我不知道如何解释。我认为它以某种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,”巴伦博伊姆说。

大厅是献给去年去世的法国前卫音乐家兼巴伦博伊姆的朋友皮埃尔·布列兹(Pierre Boulez)的,并将为学院的90名学生提供空间,他们都来自中东。它推广现代和当代音乐,其具有挑战性的节目可能会在德国找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热情观众。然而,巴伦博伊姆——一如既往的不安、好奇、严谨——几乎没有忽视核心古典曲目。
“我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发现了Elgar和Jacqueline,我做了很多,”他说。“然后我去了巴黎、芝加哥、柏林,我正在做其他类型的剧目,但记忆一点一点地回来了。”巴伦博伊姆回忆起英国管弦乐队与埃尔加的“复杂关系”,但表示他在国家管弦乐团找到了“适合这种音乐的理想管弦乐队”。“他们具有时代精神,即马勒和他的陪伴,他们了解埃尔加自身个性的特殊性。”
巴伦博伊姆没有失去活力,当我注意到英国许多人认为埃尔加音乐的爱国热情有点令人尴尬时,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民族主义抬头的主题,我大声怀疑他是否曾担心他的团结努力可能会被认为是徒劳的。“在我的生活中,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,我不会通过是否被普遍接受来判断我的所作所为。我想我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,他们得到了掌声,”他笑着说,“有些事情我可能做得很好,但他们没有。”
原创文章,作者:Mr Blues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tiqin.com.cn/1566.html